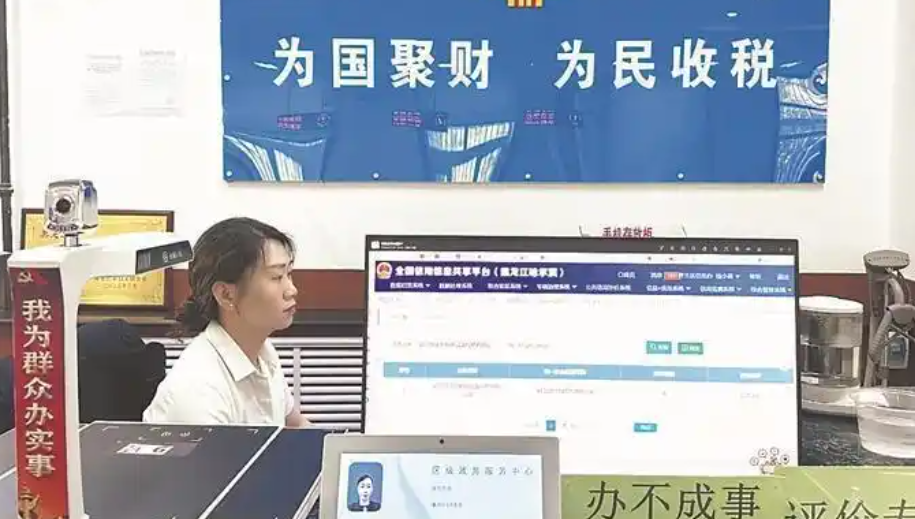二、新矛盾对法治社会建设的新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判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6]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需求方 (人民需要) 的角度来看,以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转化为对“美好生活需要”,而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都直接或间接关涉法治及其涵盖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安全环保等法治文明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广义的法律调整和法治运行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是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应当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的现实问题,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经济、法治文化、法治生态和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7]另一方面,从供给方 (法治生产) 来看,我国社会以往“落后的社会生产”供给,已经转化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态势,这里的发展,包括了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法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发展以及新发展理念要求的“五大发展”等各个方面。在法治供给方面,集中体现在我们党通过依法执政和领导法治发展提供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性供给,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立法体系现代化和科学民主立法提供的法律法规供给,国家行政机关通过行政体制和行政能力现代化以及依法行政提供的执法服务供给,国家司法机关通过司法体制和司法能力现代化以及公正司法提供的公正裁判、定纷止争的司法正义供给,全体公民通过信法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树立法治信仰形成自觉守法的秩序供给,执政党通过提高依法执政和依规治党的执政能力提供治国理政的政治供给等等,基本上都既存在法治供给不充分、不到位和不及时的问题,也存在法治供给和法治资源配置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合理的问题。
这其中,许多问题是属于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回应和解决的法治问题。
其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本质上就是建设法治社会要调整、应对和解决的社会基本问题。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法治是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法治社会不是没有矛盾、没有风险、没有冲突、没有纠纷的乌托邦、理想国的社会,而是必然会产生矛盾、存在风险、出现冲突、发生纠纷的社会。[8]面对这些风险、矛盾和问题,建设法治社会的积极意义在于,执政党、国家、社会和公民能够理性对待,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等人类法治文明的手段举措加以防范和解决。法治社会虽然不能从宏观上直接调整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但它可以从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分配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秩序等中观和微观方面,为回应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具体的法治保障和深厚的法理支撑。
其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社会新矛盾的新需要,实质上都是法治范畴需要关注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建设法治社会应当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法治社会应当是民主社会、和谐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社会、平安社会、生态文明社会、幸福社会。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既从社会发展的多方面、多角度、多领域对法治社会建设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新期待,也从法治建设的多环节、多层次、多学科对如何建设法治社会提出了新目标、新要求和新任务。党的十九大作出新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断,对于法治社会建设而言,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其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社会实践中,突出表现为在法治建设中,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用法、护法等环节的不平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家法律法规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等五大体系的不平衡;在依法治国总体布局中,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政党、法治文化等方面的不平衡;在法治改革中,司法改革、法治政府建设、立法发展、依法执政、法治监察等领域的发展不平衡;在司法改革中,法院改革、检察院改革、公安体制改革、司法行政改革等部门改革的不平衡;在法治建设具体实践中,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不同区域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领域之间、东西南北中之间等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我国法治发展的这些不充分不平衡,必然从方方面面影响、掣肘和制约法治社会建设。例如,科学民主立法供给不充分,将使法治社会建设缺少必要的法律依据和合法性前提;法治政府建设不到位,将直接影响法治社会建设的一体化和相互促进的发展进程;公正司法未实现,将具体影响人民群众通过每一个司法案件对法治社会公平正义的感受和认知,等等。
法治社会建设与社会建设、乡村建设相辅相成、殊途同归。党的十九大高度重视社会建设,明确提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9]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部分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0]在我国,城市的社会治理和农村的乡村治理,是基层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两个方面军,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两大基础性领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质上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应当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下,进一步创新法治社会建设的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在法治社会建设的治理理念上,应当更加重视引入现代治理中的“他治、自治和共治”理念和范式,减少他治,重视自治,强化共治,推进基层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在法治社会建设的治理手段上,应当更加重视大数据、互联网、信息化、云计算等高科技手段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推广和运用,把法治与“网治”“数治”“科治”“信息治”紧密结合起来,为法治社会建设插上现代高科技的翅膀;在法治社会建设的治理规范上,应当更加重视发挥法治与德治、法律与道德、硬法与软法、国家法与民间法、成文法与习惯法、公法与私法等规范规则的共同治理作用,形成以法治和法律为主导的多种规则规范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全方位治理的格局,切实把法治社会建设和依法依规治理的重心下移到乡村、社区、街道、厂矿、学校等基层单位,不断夯实法治中国建设的法治社会基础。
总之,法治社会建设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必须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对法治社会建设 (如平安、稳定、秩序、公平、正义、和谐、幸福、尊严等) 的新需要,积极回应和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法治社会建设领域出现的法治供给不充分、法治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积极打造法治社会建设转型升级的2.0版。